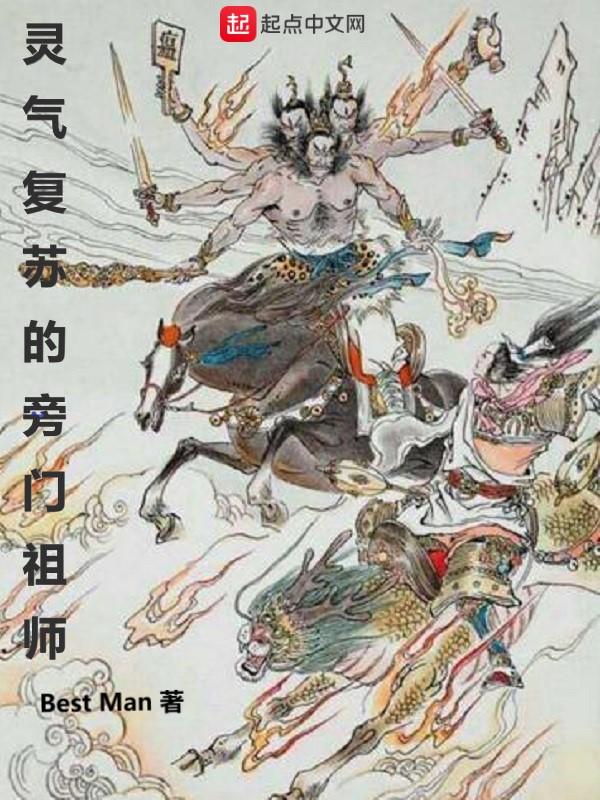悠哉小说网>重生我老婆是天后 张友笔趣阁 > 第1123章划算三(第1页)
第1123章划算三(第1页)
第二天一大早。
魅影总部老板办公室中,姜大虎看着自己小女婿为魅影即将发布的新品写的演讲词,整个人都处在惊愕交加的状态中。
全编下来,出现了无数个他都看不懂的新名词。
“2D纯屏极窄边。。。
朵朵的小脑袋靠在范真真的肩上,一路哼着幼儿园新学的歌。那是一首关于春天和小树苗的儿歌,调子轻快,像溪水从山间蹦跳而下。范真真听着,嘴角不自觉地扬起。她记得这旋律??是《她说》播客第三季里,一位母亲教女儿唱的,用来安抚噩梦后的哭泣。如今它成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口中清亮的音符。
回到家中,阳光斜斜地穿过客厅,照在书架最底层那个铁皮盒上。那是朵朵的“秘密盒子”,里面装着她的画、手工课做的纸花,还有范真真给她录的一段段语音日记。“今天我帮老师收了彩笔。”“今天我没有哭,因为我记得妈妈说,害怕也没关系。”每一段,范真真都存了备份,在“声音种子包”的私人档案里,编号#001。
她刚把朵朵放进沙发,手机又响了。林晓雨发来一段录音链接,标题只有三个字:“周婉。”
点开后,是云南山区一间木屋内的环境音。风穿过竹帘,狗吠遥远,然后是一个熟悉又久违的声音,低缓却清晰:“……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等我回来。对不起,我躲得太久了。”
范真真闭上眼,指尖轻轻摩挲屏幕边缘。周婉,曾是“桥计划”最早的五位“守护人”之一,三年前在云南某县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妇女互助小组。后来,她丈夫的家族以“败坏族誉”为由施压,村中长老召开“家法会”,逼她公开认错。她没认,却也没再露面。有人说她逃去了缅甸,有人说她疯了,也有人说她死了。
可现在,她回来了。
录音继续播放:“我在深山里住了两年。白天采药,晚上听你们的播客。每一期我都听了,尤其是那一期叫《爸爸的手》的。有个男孩说,他爸爸打完妈妈后,会坐在门槛上抽烟,一句话不说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我爸,也想起了我儿子看着我的眼神……那种恐惧,像刀子一样扎进来。”
她停顿了很久,呼吸声变得沉重。
“我不是英雄。我逃跑过,沉默过,甚至劝别的姐妹‘忍一忍就过去了’。但那天夜里,我梦见我女儿站在火堆边,手里拿着一根蜡烛,问我:‘妈妈,光是你给的吗?还是你一直藏着不敢点?’我醒来时,哭了整整一个小时。”
“我现在在乡卫生所临时住下。妇联的同志已经联系我,我想重新开始。不是为了赎罪,是为了让那些还在柜子里发抖的女人知道??就算跌进泥里,也能爬出来。”
录音结束,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。范真真睁开眼,目光落在墙上那幅地图上。云南,滇西边境,一个新的红点正在闪烁??那是系统自动标记的信号源位置。
她立刻拨通林晓雨电话:“启动‘归途’预案。医疗评估、心理支持、媒体策略同步准备。不要派陌生人去接她,让她自己决定见谁、不见谁。”
“她提了一个条件。”林晓雨声音微颤,“想见朵朵。”
范真真怔住。
“她说,朵朵是第一个听她讲故事的孩子。那时候朵朵才四岁,在一次线下活动上,别的孩子都怕她??因为她脸上有道疤,是被丈夫用烟头烫的。可朵朵走过去,摸了摸她的脸,说:‘姐姐,疼不疼?’然后递给她一颗糖。”
记忆如潮水涌来。那天的阳光很暖,朵朵穿着黄色小裙子,笑得像朵向日葵。周婉抱着她哭了很久,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当作“姐姐”,而不是“那个倒霉女人”。
“告诉她,”范真真轻声说,“朵朵每天都在等她讲新的故事。”
挂断电话,她蹲下身,打开朵朵的铁皮盒,取出一张画。那是去年儿童节的作品,题目是《我的朋友们》。画上有五个女人牵着手,站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。其中一个戴着头巾,脸上有红线,手里举着喇叭;另一个坐着轮椅,正教一个小女孩写字;还有一个背着药箱,蹲在帐篷前量血压。最右边,是朵朵和范真真手拉手,头顶写着:“妈妈说我可以当英雄。”
范真真把画贴在冰箱上,用磁铁压好。然后她打开电脑,调出“代际疗愈工程”的最新数据面板。全国已有十二个省份完成首轮教师培训,超过八万名基层工作者注册成为“倾听志愿者”。而在西藏那曲,一名曾经因家暴失语的藏族妇女,刚刚通过“声音种子包”AI系统,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远程心理咨询。
但她也知道,暗流从未停止。
三天后,公安部通报一起跨省拐卖案,解救十七名妇女,其中三人曾是“红屋角”联络员。她们被以“介绍工作”为名诱骗出境,途中遭殴打、电击、药物控制。令人痛心的是,其中有两人曾在项目结业典礼上作为代表发言,讲述如何重建生活。
范真真连夜召集危机会议。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救援现场视频:昏暗仓库里,铁链缠绕手腕,地上散落着撕碎的《她说》播客打印稿。一页纸上还留着血指印,上面写着:“我们不是货物。”
“这不是倒退,是反扑。”她在会上说,“当我们点亮一盏灯,总会有人想把它打翻。但我们要让他们明白??灯可以灭,火种不会熄。”
她下令启动“燎原行动”:在全国三百个高风险地区增设隐蔽报警点,联合通信公司开发离线语音存储功能,确保即便断网断电,求助信息也能在恢复连接后自动上传。同时,推动最高检将“系统性压迫女性人格”纳入公诉范畴,不再仅以个体伤害定罪。
与此同时,周婉的身体检查结果出来了:营养不良、慢性胃炎、左耳听力受损,心理评估显示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中度。但她坚持参加第一场回归分享会。
地点选在昆明一所女子职业学校礼堂。五百个座位全部坐满,走廊站满了人。有学生,有社工,也有曾经受助的女性。范真真抱着朵朵坐在前排。
灯光暗下,周婉走上台。她穿一件素色蓝布裙,头发简单挽起,脸上疤痕依旧明显,但眼神清澈坚定。
“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回来?”她开口,声音不大,却穿透全场,“因为我不想再做一个躲在梦里的幽灵。我想活在真实里,哪怕真实很痛。”
她讲述了这两年的逃亡生活:如何在深山里靠采药维生,如何偷偷用旧手机下载《她说》,如何在一个雪夜里,听见范真真读一封小女孩的信??“妈妈昨天又吐血了,可她说不能去医院,怕爸爸发现她报了警”??那一刻,她砸了自己藏了两年的酒瓶,烧掉了所有逃避的念头。
“我不是来拯救谁的。”她说,“我是来告诉你们,一个被打碎过的人,依然可以拼回去。不一定完整,但一定比从前更懂光的意义。”
台下有人抽泣,有人默默举起手,做出“我也是”的手语。
朵朵突然挣脱范真真的怀抱,跑上台去。全场寂静。只见她踮起脚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草莓糖,塞进周婉手里。
“姐姐,吃糖就不苦了。”她说。
周婉蹲下,紧紧抱住她,眼泪终于落下。
那一刻,直播信号传遍全国。微博瞬间爆破,“#周婉回来了#”冲上热搜第一。无数女性留言:“我也要回家了。”“我明天就去报警。”“我终于敢告诉我女儿,妈妈不是懦弱,是太累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