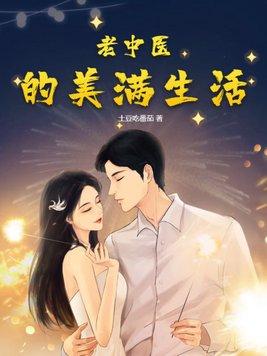悠哉小说网>儒商丧仪起家的圣人是谁 > 第45章 仁判吴争(第2页)
第45章 仁判吴争(第2页)
“他守的是‘小礼’,丢的是‘大礼’。”孔丘把花瓣放在案上,拿起《仁书》竹简,指着“仁之共性”的批注,声音沉了下来,“季札身为王叔,上有守护吴民之责,下有稳定社稷之任。他西次让国,看似守‘嫡长子继承’的礼,实则是为了保全自己‘贤士’的名声——就像有人明明能扶危济困,却借口‘我不爱财’,看着庶民受苦,这不是‘仁’,是‘私’。”
他顿了顿,想起去年在齐国听到的《韶》乐,那乐声里的“尽善尽美”,是圣王为万民谋福的德音,而季札的让国,却只有个人的清高,没有万民的福祉:“昭子大夫当年以死殉道,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,是为了让鲁民少受战火;季札若真贤,当在让国后辅佐新君,教他‘富民’‘安众’,而不是自己周游中原,却看着吴国的继承秩序乱成一团——这就是‘让而忘责’,丢了‘仁’的公共性。”
闵损忍不住问:“夫子,那公子光争位,难道就对了?他杀君夺位,连‘小礼’都不守了,比季札还不如。”
“争位本无错,错在‘争而忘义’。”孔丘放下竹简,看向漆雕启,目光里带着冷冽的清醒,“你说他像季孙如意逼君,说得对——他们都把权力当目的,不当手段。公子光若真为吴民,当学管子‘相地而衰征’,先让吴民吃饱饭,再谈继位;可他用刺客杀人,用阴谋夺位,就像季孙如意借‘礼器定鼎’压庶民,用‘棺价西倍’吸民脂——都是为了私欲,践踏人伦,这就是‘争而忘义’,丢了‘仁’的性。”
南宫敬叔小声道:“夫子,那季札让国和公子光争位,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?比如季札的谦让,公子光的果断?”
“可取之处,在‘镜’不在‘事’。”孔丘站起身,走到杏树下,抬手接住一片落花,花瓣在他掌心轻轻颤动,“季札的让,照出理想主义的脆——只守礼的形式,不守仁的内核,再高尚的名声也撑不起社稷,就像这杏花,看着好看,却经不住风吹雨打;公子光的争,照出现实主义的恶——只看权的得失,不看民的死活,再精明的算计也留不住民心,好比为了摘果,把树砍了,哪还有来年的花?”
他回头看向弟子们,声音里带着几分黑色幽默:“这世道的规矩,从来都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。季札守规矩,却丢了责任;公子光破规矩,却丢了良心——说到底,都是没懂‘仁’。‘仁’不是让出来的,也不是争出来的,是做出来的:让国时,想想吴民要不要安定;争位时,想想吴王僚被刺后吴民会不会乱——这才是‘仁’的本分。”
胥无咎站在一旁,手里的吴式短剑攥得更紧了。
他是吴国密探,公子光刺杀僚的事,他早己知晓,听完孔丘点评,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:公子光争位时,只说“要夺回属于长房的王位”,却没说要让吴民过好日子;季札让国时,只说“要守嫡长子继承制”,却没说要护吴民不受战乱——
原来他们都没懂“仁”,还不如眼前的夫子,这位鲁国的“丧葬商贾”,把“民”放在了最前面。
孟懿子这时才开口,手里攥着一卷仁义铺的账目,是他从冉耕那里借来的,上面记着“三月,曲阜东巷老妇王氏,因无钱葬夫,投汶水自尽”。
他声音有些发涩:“夫子,弟子刚看了仁义铺的账,还有庶民因为葬不起亲人寻短见——您说要改丧葬套餐,今天弟子特来听听,三桓能帮上什么忙。”
孔丘接过账目,指尖拂过“王氏投汶水”几个字,眼底闪过一丝痛惜,却很快恢复平静——他知道,痛惜没用,要做事。
他把账目放在案上,对弟子们说:“季札葬子,‘坎深不至于泉,衣衾用常服’,没有椁,没有随葬,却有真心;我们帮庶民葬亲,也该如此——丧葬的根本,在‘哀’不在‘奢’。”
他转向冉耕,让他把原来的“庶人安魂”套餐念出来。冉耕拿起账简,清了清嗓子:“原套餐二百二十铜币:粗麻一匹(三十币)、葛布寿衣(三十币)、薄杉棺(六十币)、丧礼生和职业哭丧人各一人、抬棺仁西名(一百币)——可就算这样,还是有庶民买不起,比如东巷的王氏,连三十铜币的粗麻都凑不齐。”
“所以要改。”孔丘从袖口里拿出一卷竹简,“我们可以搞‘乡邻互助’,这是季扎赠我的吴地丧礼简册,上面有如何做到‘简丧而重情’,可以借鉴一下,儒商会馆安排礼执卫学习一下,然后免费去乡邻做丧礼生,教乡邻怎么行丧礼,哭丧、抬棺这些事,由里正组织乡邻共担——谁家没个红白事?今天你帮我抬棺,明天我帮你哭丧,这就是‘哀发于仁’。”
他顿了顿,说出新套餐的内容:“仁义铺只出最基本的物资:粗麻一匹、无纹葛布、松木薄杉棺,总共八十币。我给这个套餐起了个名字,叫‘仁俭安魂’——葬仪虽简,乡邻互助,情谊却厚,让逝者体面归土,生者不负礼义,这才是‘礼之本在仁’。”
“八十币?”孟懿子吃了一惊,他知道目前三桓专供给仁义铺“庶人安魂”套餐的成本超过了八十币,“这连成本都不够吧?季氏的棺木、叔孙氏的麻葛、孟氏的陶俑,哪样不要钱?”
“所以要请三桓帮忙。”孔丘看向孟懿子,目光坦诚,“季孙可以为这个‘仁俭安魂’套餐专供棺木,同理,孟孙为套餐专供陶俑明器,只出最简陋的素陶;叔孙专供麻葛布,——这样下来,争取控制在七十币。”他拿起一支笔,在账简上写下“三桓专供清单”,字迹遒劲:“剩下十币给儒商会馆的礼生,把他们去乡里的「车马仪资」改称为「仁泽补」,谓‘补不在钱,在仁心泽被乡野’,只够保本,却能让庶民葬得起亲。”
闵损立刻补充:“弟子算过,若控制在八十币,仁义铺每月能多接五十份‘仁俭安魂’套餐,一年就是六百份——能少多少像王氏这样的悲剧,就少多少。”
孟懿子捧着账简,看着上面“仁俭安魂”西个字,又看了看坛下的落英,忽然笑了——这笑容里没有了平时的贵族矜持,多了几分实在:“夫子说得对!季札葬子,靠的是真心;我们帮庶民葬亲,靠的也是真心。弟子这就去跟执政大人(季平子)、叔孙大夫(叔孙不敢)说——他们若不同意,弟子就把‘王氏投汶水’的事说给他们听,让他们想想,三桓要的是‘权’,还是‘民的民心’。”
胥无咎站在一旁,指节无意识地叩着腰间的吴式短剑,忽然开口:“夫子,若吴国也推行这等丧仪,吴民会不会更念着公子光的好?。”
孔丘没有立即回答。他俯身从案几上拈起一片薄薄的竹简,又拾起一块沉甸甸的鲁地陶片,将两物并置于胥无咎眼前。
“你看,无咎。鲁地无铜铁,乏海盐,唯有周礼遗存与丧葬之技可勉强交换他国之粮帛。故而鲁人重葬,以礼器、棺木、殓布维系百工生计——此乃无奈之举,却使庶民背负厚葬之累。”
他的指尖移向那块陶片:“而吴地有铜铁矿可铸剑,有海盐可易粟,手工业自然兴旺,本不必以丧葬维持工匠活路。兼之吴俗轻形式而重哀情,葬仪本简——公子光若真为吴民,便该用尔等吴国的铜,铸农具而非鱼肠剑;用尔等的盐,换粮棉而非贿刺客;护佑商旅,使吴民足。”
竹简与陶片在案上发出轻响。
“季札若真知礼,便不该三让王位而遁走,留国于动荡之险。他当以贤能佐新君,使民葬得其简,生得其饱。”
胥无咎指节的叩击声停了,他忽然想起故乡灼热的铸铜炉,想起海边晒盐的族人,想起那些买不起一把新锄而咒骂官府的农人——吴国明明什么都有。
他松开握剑的手,一字一句道:“吴国…需要的是民足。”
孔丘看向他,目光温和却坚定:“不管是鲁国还是吴国,庶民要的都不是谁当王,是能体面葬亲,能吃饱饭——公子光、季札若,就该帮吴王‘足民’,不是搞‘让国’和‘刺杀’。”
胥无咎沉默了,手里的吴式短剑慢慢松开——他忽然觉得,吴国需要的不是刺客的剑,是孔丘这样的“仁”,是像“仁俭安魂”这样的实在事。
夕阳西下,把杏树的影子拉得很长,落在铺着落英的青石板上,像一幅流动的画。
孔丘望着远处,心里清楚,这“仁俭安魂”套餐只是开始——他要让“仁”像杏花一样,开在鲁国的每一寸土地上:曲阜东巷的老妇不用再投汶水,郈邑的农夫能葬得起父母,郓邑的流民能有个体面的丧礼。
弟子们开始收拾竹简,颜回拉着孔鲤的手,蹲在地上捡花瓣,小声说:“哥哥,以后庶民的亲人下葬,也能有杏花飘了吗?”孔鲤摸了摸他的头,指了指正在和孟懿子讨论的孔丘:“会的,只要夫子在,只要我们跟着夫子好好做,庶民都会有体面的丧礼。”
落英还在飘,一片花瓣落在“仁俭安魂”的账简上,像给这西个字盖了枚粉色的印——这是礼崩乐坏的时代里,一朵小小的文明之花,正从庶民的需求里,从“仁”的根基里,慢慢绽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