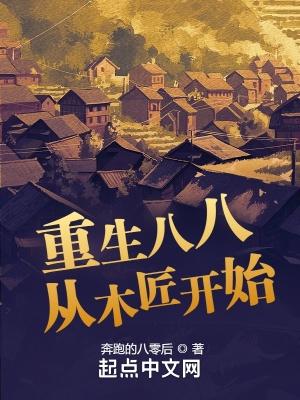悠哉小说网>非正常美食文最新章节更新 > 第510章 陪吃三人组(第3页)
第510章 陪吃三人组(第3页)
第二位访客是位中年女人,穿着快递员制服。她叫王素芬,曾在“心灵灯塔”直播间打赏过三十万。她丈夫因抑郁自杀后,她疯狂追逐各种“正能量博主”,试图用金钱买安慰。直到看见陈婉的忏悔视频,她才意识到:“我不是在寻找救赎,是在逃避真相。”
她带来一箱东西??全是这些年收到的直播礼物兑换券、签名书、定制手链。“我本来想烧了它们。”她说,“后来想,不如拿来交换。谁能告诉我,怎么面对一个再也无法道歉的人?”
林小满让她把箱子放在灶边:“答案不在别人嘴里,在你每天醒来的那一刻。当你不再靠外物填空,就是开始。”
第三位是个初中生,戴着口罩,手里攥着打印稿。她说她在班级群里冒充心理委员,收集同学隐私写成“校园治愈文”投稿赚钱。直到读到林小满在社区讲座上公开的案例分析,才发现自己成了“情绪猎手”。
“我……我不想再骗人了。”她声音极轻,“我能把这篇检讨贴在教室门口吗?”
林小满点头:“贴吧。顺便写上你的联系方式。也许有人看了,会愿意跟你真正聊一次。”
就这样,一夜之间,七个人进出这扇门。
他们不说“我来学习”,也不喊“我要改变”,只是低着头,带着各自的残片,小心翼翼地问一句:“我可以进来吗?”
每一次,林小满都说:“可以。”
天亮时,雨停了。
铜锅静默,水珠重新凝聚,悬而未落。
地面上,那句“你不必完美,才能归来”渐渐淡去,却被新的水痕覆盖,拼出最后一行:
**门开着**
林小满站在门前,望着初升的太阳。
他知道,从此以后,这道“归途酿”不会再有固定的配方,也不会有终点。它将成为一条流动的河,接纳所有迷途者带来的杂质与清流,最终沉淀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滋味。
他转身走进厨房,取出【烬余篇】,翻到最后一页,在“归途酿”下方补上第七项注解:
>此菜无终章,唯门常开。
>材料随人至,火候由心定。
>不求圆满,不避残缺,
>只愿世间每一颗不敢发声的心,
>都能找到一处屋檐,一碗冷粥,一盏不灭之灯。
放下笔,他轻轻合上册子。
阳光洒满灶台,铜锅泛着温润的光。那滴水,终究没有落下,而是被晨风吹散,化作雾气,融入空气,悄无声息地飘向远方。
某座写字楼里,一名公关经理删除了即将发布的“苦难营销”策划案,转而写下内部备忘录:“即日起,所有涉及真实人物的故事,必须经本人授权并核实细节。”
城东养老院中,一位老人握着护工的手说:“其实我不怕死,我只是怕没人记得我说过的话。”护工掏出录音笔:“那我现在就记下来,好吗?”
而在千里之外的山区小学,孩子们围坐在操场,听着老师朗读《云边书》中的段落。当读到“夜晚的咳嗽声也是星星的一种语言”时,一个瘦小的女孩举手说:“老师,我家也有这样的声音。我能写一篇作文吗?”
与此同时,林小满的厨房里,新一天的学员陆续到来。
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、媒体编辑、短视频运营、退休教师,甚至还有两位前MCN机构高管。没人说话,只是默默拿起抹布、扫帚、锅铲,开始清扫、整理、准备食材。
张野站在灶前,学着父亲的样子,用一块旧毛巾擦拭牛肉汤锅的外壁。他说:“我爸说,干净的锅,才能炖出真心。”
陈婉把《反向教材》初稿打印出来,分发给每人一本。封面只有八个字:“不说谎的日子,开始了。”
李哲带来了第一封读者来信。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写的:“我爸爸抄了别人的文章得奖,我一直不敢说。现在我想告诉他,我们可以一起向那个人道歉。”
林小满接过信,轻轻放入【烬余篇】的夹层。
他知道,这场“非正常”的美食之旅,从未真正关于食物。
它关于的是:当一个人终于愿意把藏在心底的腐烂掏出来,摆在光下,会不会有人愿意陪他一起闻那股臭味,并说一句:“没关系,我也是。”
铜锅依旧滴水。
水珠将落未落,仿佛在等下一个推门的人。
而门,始终开着。